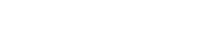呼吸焦灼,暧昧不明。
陶桃怔怔地盯着他看,呼吸逐渐平稳,恢复了正常,原本攀在简亓肩上的手轻垂了下来,半推半就变成抵抗防御的动作。
手碰上他上衣的纽扣,恰好能感受到心跳的脉搏此起彼伏,内里汹涌着的血气方刚最是热烈。
“去吃饭吧。”
那人将视线从红透的耳侧再移到唇间,刚刚他吃尽上面仅存的最后一点唇彩,一到动情的时刻,无可控制地由交缠变成吮咬。
歉疚冒了出来,怜惜盖过情欲,从来都在两性关系里自持的男人,初次尝过因女人魂牵梦萦的滋味,也把持不住。
然后在夜不能寐的梦醒时分,看清了自己。
从不是什么圣人。
依照简亓的长相、学识、家境,从青春期的躁动的时候,就已成了不少女孩子的暗恋对象,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读书时就从没有断过桌洞里被人偷偷放置的礼物、桌上莫名出现的粉色信物。
对待异性刻意的接近,不经意刻意投来抛出橄榄枝的好意,经过这么多年,逐渐习以为常,无感且麻木。
男人都是自恋的动物,他无一例外是个俗人。
他从未有过掩饰对陶桃饶有兴趣的想法,从破天荒答应相亲安排的时候,一切如命中注定般的天翻地覆。
简亓,对爱情有成长经历的前车之鉴。
简如望从来不是一个好丈夫,更遑论是一个好父亲。
简先生的仕途一路高升,加上顾湘的娘家在本市财力雄厚,生意场需要一把庇荫大伞,简如望在官场混迹亦需要顾家支持。
三十年前,两位年少相识的年轻人一拍即合,那场婚礼盛大,来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谁都无法想象未来的日子里,这对新人的婚姻生活皆是不合的针锋相对。
故事的结尾是,简如望出轨了。
熟人作案,朝夕之间。
最开始,顾湘没有同他离婚的心力,她更是薄面的人,那个时代里,离婚的闺秀只会成为大院里受到周遭他人舆论地议论,沦为茶余饭后的笑柄,所以顾湘选择为了儿子的成长环境忍气吞声。
结果适得其反,简亓对婚姻的初始印象就是将其界定为一场充满暴力行径的囚牢。
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婚姻,是不是就是一个让快乐的人变得不幸福的过程。
简如望总有各种不回家的理由,顾湘年轻时也是气盛的性子,终究是遭不住简先生冷暴力,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
当父母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小孩自然而然地开始早慧,扮演起充当哄大人开心的角色,努力通过血缘成为关系粘结的纽带,然后在每年生日时滑稽的许愿,希望爸爸妈妈的关系可以有所缓和。
他不懂顾湘每次忽然冲他发完脾气之后立刻转变态度,开始流内疚的眼泪;不懂为何简先生每次回家都是一身酒气,而父母房中为什么总是传来整夜整夜的争吵声。
他们总是吵架,然后砸手边一切可以摔在地上的东西。
简如望在顾湘的连声质问之中失去理智,随手将茶几上可触及到的东西重重地摔向地面。
他砸落的是简亓今天参加比赛时获得的奖杯,那天简先生回家本是为了庆祝儿子得奖,简亓主动给爸爸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说妈妈还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蛋糕。
当时的简先生还是对儿子残留些怜爱之意,应允之后,还提及周末的短途旅行。
他回家,还是因为孩子妥协。
可他仍旧爽约。
顾湘让简亓先将蛋糕吃了,好不容易哄睡了孩子,一人坐在客厅等简如望回家。
她等到了。在十一点过一刻的时候。
顾湘甚至还能好脾气的上演一场郎情妾意,体恤地为他脱下外衣,道一句辛苦了。
可外套上赫然粘着的一根女性长发还是让她的情绪决堤爆发。
那天晚上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简亓夜半被声响惊醒,迷迷糊糊地从房间起来,没有开灯站在中庭听他们吵架的内容。
女人、情人、爱人、妻子、儿子。
简如望从始至终在意的只有自己。
看清地上支离破碎的奖杯碎片,简亓没了睡意,眼底亦攒满失望。
顾湘不甘示弱,又一声巨响,她砸掉了简如望在仕途中获得荣誉的第一块牌匾。
难以入耳的话一句一句往外冒了出来,顾女士还是不解气,拖鞋重重地碾在绒布上摩擦,将简如望引以为傲的政绩踩在脚底下。
“简如望,你装了这么多年,难道真的以为自己是什么正派的人物吗?”
“疯子。”简先生觉得她不可理喻,摔门而去。
顾湘跌坐在地,眼神空洞,哭花了为简先生而粉饰的妆。
简亓回到房间,装作无事发生,彻夜假寐。
后面再长大些,简亓不再奢求所谓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虚假景象,也再不会和同龄人骄傲地炫耀电视上那个被采访的人,是自己的父亲。
简作为姓氏,在临城一脉并不算常见。
人性是复杂的,简如望做出了政绩,在触及政治高压线前悬崖勒马。
他或许想选择做一个称职的人民公仆,有政治抱负的高官,但绝非是个合格的父亲。
顾家从民国便开始发迹,百年沉浮,就算如今有光辉有落寞,顾湘也是从没吃过苦的。
顾家培养出的女儿流淌着有骨气的血,比起困于屋檐下解决厨房一日三餐的琐事,更应该做优秀独立女性。
幸运的是,她忍无可忍选择了当断则断,不再祈求简如望会回心转意,在简亓八岁那年正式提出了离婚,试图结束这场荒唐的婚姻闹剧。
简先生不知究竟是舍不得岳丈势力的照拂,还是对年少恋人的妻子心怀悔意,开始以各种理由拒绝和逃避。
闹到最后,顾湘也不争了,无视这场婚姻的存在,去寻自己的理想,只要孩子是她的就行。
二十年过去,转眼简亓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
尽管家庭形态是畸形的,顾女士给的爱也是分明的,她不满简如望对待家人的作风做派,暗讽他三顾家门而不入是惺惺作态,但对于早已是鳏夫的简老爷子还是敬重的。
简家和顾家是世交,往上数几代,政商军医都有所涉及,简家虽然如今生意场上落寞了,可简老爷子年轻时也是正儿八经的军人出身。
简亓的童年,说不上支离破碎,也谈不上有多幸福。
简先生外面的女人怀孕了,在除夕夜挺着大肚子找上门来,顾湘在顾家面前维持了这么多年的体面终于分崩离析。
简亓是那场闹剧里的见证,他像一个无关紧要的闲杂人等,甚至熟稔地充当了安抚的角色,纵火点了一夜的箱装礼炮。
那本是顾家人为正月初一祛除祟气,准备的仪式,当烟花升上夜空,爆破声淹没了庭院里成年人激烈的争吵叫骂。
也掩盖了每一句涉及为儿子的前途着想这类的无意义而又虚假的蠢话废话。
至于后来的走向,他也不清楚,或许简亓现在还有个流落在外的弟弟妹妹,可谁又会在意这些?
没人在意。
生活在这样一个父爱缺位的特殊家庭,简亓又是顾家一脉的小辈里的独子,顾湘有意对他严厉一些。
简亓不负众望地没有长歪,青春期更是没有叛逆的时段,论道德感和责任感都是简家兄弟里难寻的一份正派。
所以贤者时刻,当性的出口疏解之后,他审慎地开始细想与陶桃相处的细枝末节。
毫无疑问,他对小桃老师的兴趣无需遮掩,直到锚定目标后,他也不是会轻易动摇的人。
父母的婚姻让简亓对待两性关系里立起了的危墙,都市男女,说起爱情人人自危。
但对待陶桃,他从不是说说而已,所以才会格外在意另一半的感受。
接连被躲着的那两周,小桃老师的回避是单方面的不想碰面,可在同一层办公,偶遇的机会和方式有千百种,时间长了也摸清了她的路数,识趣地有意控制不出现在她的视线之内。
他无法做到不关注她的动向,于是有了一次又一次在身后的远望。
至于陶桃是否知晓,并不重要。
昨晚的一切,都是顺水推舟,任何进展都是情理之中。
简亓在情情爱爱这类事里是十足的笨人,他守了一夜回复,想说的话在对话框里敲敲打打,难免多想了些。
简亓之前就在私下找叶常国要过陶桃的资料,打得一手知己知彼的好牌,拿到建档时登记的资料,他的关注点自然不会是毕业院校,而是出生年月。
换算了一下差的年岁,简亓刚过了28岁的生日,而小桃老师才24岁,四舍五入实打实多活了三年半。
发小那边传来了回复,许凪远还在算为财务报表的事忙得脚不沾地,半夜三更看到简亓发疯炫耀脱单,攻击力一针见血,强得没边。
「你说说你,一个泡上刚毕业应届生的老男人,大晚上搁着发什么疯呢?」
呵,老男人。
简亓挂了电话,自嘲地开始想。
生理反应难以遏制,可人家确实还只是刚毕业工作的小姑娘,简亓开始反思,比起担忧日后的相处,他更担心过快的肢体接触会不会让她害怕。
那都可以先等一等的再做的。他并不是那么急切的人。
至于动人的情话他还也还在摸索学习,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他愿意一句句慢慢地,当面说予她听。
于是在此时,陶桃就是在接吻时皱了下眉,他都开始追悔自己的操之过急。
爱情果真是盲目。
陶桃饿过了劲,早上就没有喝几口甜汤,连着上了两节课,消化不良的肠胃煞风景地发出咕噜的叫声。
好尴尬,方才还想调情玩点暧昧的手段,在密闭环境里更是听得清楚明白,气氛被她破坏完了。
耳畔响起低声的笑意,陶桃利索地解了安全带,下车关门一气呵成。
真想找个地缝钻。
来的路上陶桃在点评上买了荣记的团购套餐,以为过了饭点,还是失策了,没想到门口还是大排长队。
陶桃还是第一次来吃荣记,之前就有听赵老师提起过这家金陵菜系,滋味在临城可以排到前几位,今日一见,人气绝非一般的火爆。
该早想到定位置的,还在踌躇间,已有迎宾的侍从迎了过来。
“简先生,这边请。”
云里雾里,直到落座,上头的牌匾写着,竹隐二字。
环境很是雅致。
陶桃肚子有些不舒服,借故想去卫生间,包厢门被人打开,许凪远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许老板原以为简亓带着侄子来吃饭,还在欠揍地想说专门为之之准备了礼物,待会儿让小孩尝尝合不合口味。
没想到迎面见到了生面孔,女人样貌姣好,长发轻盈地拢着双肩,此时见到生人,乌黑的眸子闪着无措。
该是简老师的熟人,陶桃颔首算打过招呼。
“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应届生女老师?”
简亓这些年当了老师之后气质愈发沉稳,提起陶桃毫无遮掩否认的意思,坦荡地应允后笑意直达眼底,“当然,我女朋友。”
女人离开包厢,轻声关上了门。
人一走,许凪远说话不算客气,挤眉弄眼地看着简亓,不免有些怀疑。
一个月没见,简亓竟然背着兄弟几个闷声脱了单。
好嘛,一问,竟然还是学校里的同事。
他们发小几个从小一个院里长大,许凪远身边是女色从未断过的,简亓呢,则是哥几个里面的清流。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大家该出国的出国,留在国内的也都是填了些金融、经管之类的商科专业,好毕业后继承家里产业的衣钵。
这简亓倒好,跳级不说,完全出人意料的,跑去学数学去了。
之后顺带保研,一通操作下来,他们都以为他这是要在学术上深造的架势,结果最后毕业了竟然选择回临城当起了高中老师。
实在是大跌眼镜。
许凪远没见过简亓对谁有过好感,所以当简亓和他说自己谈恋爱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不信的,之后便是好奇,那人会长什么样。
现在见到面了,人确实是美的,只是未免太素了,少了些气质做点缀。
思来想去觉得总有些不对,脱口而出问道,“你这脱单了,小梧怎么办?”
简亓不喜,斜眼睨他,“关陈桑梧什么事?”
“好好好,不关不关。”
许凪远就是看这些年简亓一直单身,如今看他有了对象,提起旧人往事,时过境迁,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起来,“你说要是小梧当时没出国,你和她会不会就···?”
“别惹我骂你。”简亓鲜少愠怒,话不是说说而已。
许凪远收住了嘴,没再说什么扫兴话。
他也就一时感慨,当时大院里发小几个就小梧一个女孩子,从小就喜欢跟在简亓的屁股后面打转,大些了简亓不住大院里了,见不到面的那几年陈桑梧消停了些。
直到后面又考到了同一个高中,又死灰复燃了。
陈桑梧追求简亓的狂热,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也看不懂简亓到底她有没有意思,碍于陈家和顾家交好,简亓从未当着大家的面驳过小梧的面子,但也从没有接受过陈桑梧对他的好。
或许是被逼得太紧,有些烦了,直接跳了级。
小梧本来就比简亓小一岁,脾气是娇纵了些,事关高考,也不敢再去烦简亓了。
再后来,简亓考去了Z大,小梧也不知为何没有再嚷嚷着立志要考去省城和简亓读同一个大学,而是选择出国念书。
许凪远不是多管闲事的人,只是这些年自己当了老板,又是做荣记这样每天和无数人打交道的生意,看透了虚与委蛇。
人呢,也没前些年那么浪了,开始觉得有个门当户对又知根知底的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简亓一直单着,最开始他们就单纯觉得他那是洁身自好,可看到小梧一个人在英国这么多年,也从没见她接触过其他新的人,也是长情。
私下里难免自然地展开联想。
毕竟当年他们谁也不知道小梧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想出国了。
前段时间陈桑梧还找过他,问起了大家最近的现状,话里话外问的,其实还是尤其关注简亓现阶段的动向。
许凪远能怎么说,说简亓这位醉心教书现在已经打出招牌来的金牌教师,现在当然还是单身咯。
一个从小被捧为掌上明珠的女孩,因为赌气跑到国外念书,他是不理解的,可是听到小梧念念不忘这么多年,至此没有回响的时候,许凪远确实也是有点有意撮合的意思。
没想到等来的是,简亓和他说,自己谈恋爱了。
造化弄人啊,许老板长叹一声,不再自讨没趣,神叨叨地说缘分可遇不可求。
临走前又遇到了简亓这小女友回来,他当即绽开了个笑容,友好地打招呼自我介绍,“你好啊,我叫许凪远。”
女孩比方才从容,音色却比他想象里的绵软,极其有礼貌地微微鞠躬,不卑不亢地回握了他的手,“你好,我叫陶桃。”
许凪远心下了然,他大概知道简亓为什么喜欢她了。
陶桃怔怔地盯着他看,呼吸逐渐平稳,恢复了正常,原本攀在简亓肩上的手轻垂了下来,半推半就变成抵抗防御的动作。
手碰上他上衣的纽扣,恰好能感受到心跳的脉搏此起彼伏,内里汹涌着的血气方刚最是热烈。
“去吃饭吧。”
那人将视线从红透的耳侧再移到唇间,刚刚他吃尽上面仅存的最后一点唇彩,一到动情的时刻,无可控制地由交缠变成吮咬。
歉疚冒了出来,怜惜盖过情欲,从来都在两性关系里自持的男人,初次尝过因女人魂牵梦萦的滋味,也把持不住。
然后在夜不能寐的梦醒时分,看清了自己。
从不是什么圣人。
依照简亓的长相、学识、家境,从青春期的躁动的时候,就已成了不少女孩子的暗恋对象,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读书时就从没有断过桌洞里被人偷偷放置的礼物、桌上莫名出现的粉色信物。
对待异性刻意的接近,不经意刻意投来抛出橄榄枝的好意,经过这么多年,逐渐习以为常,无感且麻木。
男人都是自恋的动物,他无一例外是个俗人。
他从未有过掩饰对陶桃饶有兴趣的想法,从破天荒答应相亲安排的时候,一切如命中注定般的天翻地覆。
简亓,对爱情有成长经历的前车之鉴。
简如望从来不是一个好丈夫,更遑论是一个好父亲。
简先生的仕途一路高升,加上顾湘的娘家在本市财力雄厚,生意场需要一把庇荫大伞,简如望在官场混迹亦需要顾家支持。
三十年前,两位年少相识的年轻人一拍即合,那场婚礼盛大,来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谁都无法想象未来的日子里,这对新人的婚姻生活皆是不合的针锋相对。
故事的结尾是,简如望出轨了。
熟人作案,朝夕之间。
最开始,顾湘没有同他离婚的心力,她更是薄面的人,那个时代里,离婚的闺秀只会成为大院里受到周遭他人舆论地议论,沦为茶余饭后的笑柄,所以顾湘选择为了儿子的成长环境忍气吞声。
结果适得其反,简亓对婚姻的初始印象就是将其界定为一场充满暴力行径的囚牢。
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婚姻,是不是就是一个让快乐的人变得不幸福的过程。
简如望总有各种不回家的理由,顾湘年轻时也是气盛的性子,终究是遭不住简先生冷暴力,陷入无尽的自我怀疑。
当父母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随之而来的,小孩自然而然地开始早慧,扮演起充当哄大人开心的角色,努力通过血缘成为关系粘结的纽带,然后在每年生日时滑稽的许愿,希望爸爸妈妈的关系可以有所缓和。
他不懂顾湘每次忽然冲他发完脾气之后立刻转变态度,开始流内疚的眼泪;不懂为何简先生每次回家都是一身酒气,而父母房中为什么总是传来整夜整夜的争吵声。
他们总是吵架,然后砸手边一切可以摔在地上的东西。
简如望在顾湘的连声质问之中失去理智,随手将茶几上可触及到的东西重重地摔向地面。
他砸落的是简亓今天参加比赛时获得的奖杯,那天简先生回家本是为了庆祝儿子得奖,简亓主动给爸爸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回家,说妈妈还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蛋糕。
当时的简先生还是对儿子残留些怜爱之意,应允之后,还提及周末的短途旅行。
他回家,还是因为孩子妥协。
可他仍旧爽约。
顾湘让简亓先将蛋糕吃了,好不容易哄睡了孩子,一人坐在客厅等简如望回家。
她等到了。在十一点过一刻的时候。
顾湘甚至还能好脾气的上演一场郎情妾意,体恤地为他脱下外衣,道一句辛苦了。
可外套上赫然粘着的一根女性长发还是让她的情绪决堤爆发。
那天晚上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简亓夜半被声响惊醒,迷迷糊糊地从房间起来,没有开灯站在中庭听他们吵架的内容。
女人、情人、爱人、妻子、儿子。
简如望从始至终在意的只有自己。
看清地上支离破碎的奖杯碎片,简亓没了睡意,眼底亦攒满失望。
顾湘不甘示弱,又一声巨响,她砸掉了简如望在仕途中获得荣誉的第一块牌匾。
难以入耳的话一句一句往外冒了出来,顾女士还是不解气,拖鞋重重地碾在绒布上摩擦,将简如望引以为傲的政绩踩在脚底下。
“简如望,你装了这么多年,难道真的以为自己是什么正派的人物吗?”
“疯子。”简先生觉得她不可理喻,摔门而去。
顾湘跌坐在地,眼神空洞,哭花了为简先生而粉饰的妆。
简亓回到房间,装作无事发生,彻夜假寐。
后面再长大些,简亓不再奢求所谓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虚假景象,也再不会和同龄人骄傲地炫耀电视上那个被采访的人,是自己的父亲。
简作为姓氏,在临城一脉并不算常见。
人性是复杂的,简如望做出了政绩,在触及政治高压线前悬崖勒马。
他或许想选择做一个称职的人民公仆,有政治抱负的高官,但绝非是个合格的父亲。
顾家从民国便开始发迹,百年沉浮,就算如今有光辉有落寞,顾湘也是从没吃过苦的。
顾家培养出的女儿流淌着有骨气的血,比起困于屋檐下解决厨房一日三餐的琐事,更应该做优秀独立女性。
幸运的是,她忍无可忍选择了当断则断,不再祈求简如望会回心转意,在简亓八岁那年正式提出了离婚,试图结束这场荒唐的婚姻闹剧。
简先生不知究竟是舍不得岳丈势力的照拂,还是对年少恋人的妻子心怀悔意,开始以各种理由拒绝和逃避。
闹到最后,顾湘也不争了,无视这场婚姻的存在,去寻自己的理想,只要孩子是她的就行。
二十年过去,转眼简亓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
尽管家庭形态是畸形的,顾女士给的爱也是分明的,她不满简如望对待家人的作风做派,暗讽他三顾家门而不入是惺惺作态,但对于早已是鳏夫的简老爷子还是敬重的。
简家和顾家是世交,往上数几代,政商军医都有所涉及,简家虽然如今生意场上落寞了,可简老爷子年轻时也是正儿八经的军人出身。
简亓的童年,说不上支离破碎,也谈不上有多幸福。
简先生外面的女人怀孕了,在除夕夜挺着大肚子找上门来,顾湘在顾家面前维持了这么多年的体面终于分崩离析。
简亓是那场闹剧里的见证,他像一个无关紧要的闲杂人等,甚至熟稔地充当了安抚的角色,纵火点了一夜的箱装礼炮。
那本是顾家人为正月初一祛除祟气,准备的仪式,当烟花升上夜空,爆破声淹没了庭院里成年人激烈的争吵叫骂。
也掩盖了每一句涉及为儿子的前途着想这类的无意义而又虚假的蠢话废话。
至于后来的走向,他也不清楚,或许简亓现在还有个流落在外的弟弟妹妹,可谁又会在意这些?
没人在意。
生活在这样一个父爱缺位的特殊家庭,简亓又是顾家一脉的小辈里的独子,顾湘有意对他严厉一些。
简亓不负众望地没有长歪,青春期更是没有叛逆的时段,论道德感和责任感都是简家兄弟里难寻的一份正派。
所以贤者时刻,当性的出口疏解之后,他审慎地开始细想与陶桃相处的细枝末节。
毫无疑问,他对小桃老师的兴趣无需遮掩,直到锚定目标后,他也不是会轻易动摇的人。
父母的婚姻让简亓对待两性关系里立起了的危墙,都市男女,说起爱情人人自危。
但对待陶桃,他从不是说说而已,所以才会格外在意另一半的感受。
接连被躲着的那两周,小桃老师的回避是单方面的不想碰面,可在同一层办公,偶遇的机会和方式有千百种,时间长了也摸清了她的路数,识趣地有意控制不出现在她的视线之内。
他无法做到不关注她的动向,于是有了一次又一次在身后的远望。
至于陶桃是否知晓,并不重要。
昨晚的一切,都是顺水推舟,任何进展都是情理之中。
简亓在情情爱爱这类事里是十足的笨人,他守了一夜回复,想说的话在对话框里敲敲打打,难免多想了些。
简亓之前就在私下找叶常国要过陶桃的资料,打得一手知己知彼的好牌,拿到建档时登记的资料,他的关注点自然不会是毕业院校,而是出生年月。
换算了一下差的年岁,简亓刚过了28岁的生日,而小桃老师才24岁,四舍五入实打实多活了三年半。
发小那边传来了回复,许凪远还在算为财务报表的事忙得脚不沾地,半夜三更看到简亓发疯炫耀脱单,攻击力一针见血,强得没边。
「你说说你,一个泡上刚毕业应届生的老男人,大晚上搁着发什么疯呢?」
呵,老男人。
简亓挂了电话,自嘲地开始想。
生理反应难以遏制,可人家确实还只是刚毕业工作的小姑娘,简亓开始反思,比起担忧日后的相处,他更担心过快的肢体接触会不会让她害怕。
那都可以先等一等的再做的。他并不是那么急切的人。
至于动人的情话他还也还在摸索学习,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他愿意一句句慢慢地,当面说予她听。
于是在此时,陶桃就是在接吻时皱了下眉,他都开始追悔自己的操之过急。
爱情果真是盲目。
陶桃饿过了劲,早上就没有喝几口甜汤,连着上了两节课,消化不良的肠胃煞风景地发出咕噜的叫声。
好尴尬,方才还想调情玩点暧昧的手段,在密闭环境里更是听得清楚明白,气氛被她破坏完了。
耳畔响起低声的笑意,陶桃利索地解了安全带,下车关门一气呵成。
真想找个地缝钻。
来的路上陶桃在点评上买了荣记的团购套餐,以为过了饭点,还是失策了,没想到门口还是大排长队。
陶桃还是第一次来吃荣记,之前就有听赵老师提起过这家金陵菜系,滋味在临城可以排到前几位,今日一见,人气绝非一般的火爆。
该早想到定位置的,还在踌躇间,已有迎宾的侍从迎了过来。
“简先生,这边请。”
云里雾里,直到落座,上头的牌匾写着,竹隐二字。
环境很是雅致。
陶桃肚子有些不舒服,借故想去卫生间,包厢门被人打开,许凪远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许老板原以为简亓带着侄子来吃饭,还在欠揍地想说专门为之之准备了礼物,待会儿让小孩尝尝合不合口味。
没想到迎面见到了生面孔,女人样貌姣好,长发轻盈地拢着双肩,此时见到生人,乌黑的眸子闪着无措。
该是简老师的熟人,陶桃颔首算打过招呼。
“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应届生女老师?”
简亓这些年当了老师之后气质愈发沉稳,提起陶桃毫无遮掩否认的意思,坦荡地应允后笑意直达眼底,“当然,我女朋友。”
女人离开包厢,轻声关上了门。
人一走,许凪远说话不算客气,挤眉弄眼地看着简亓,不免有些怀疑。
一个月没见,简亓竟然背着兄弟几个闷声脱了单。
好嘛,一问,竟然还是学校里的同事。
他们发小几个从小一个院里长大,许凪远身边是女色从未断过的,简亓呢,则是哥几个里面的清流。
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大家该出国的出国,留在国内的也都是填了些金融、经管之类的商科专业,好毕业后继承家里产业的衣钵。
这简亓倒好,跳级不说,完全出人意料的,跑去学数学去了。
之后顺带保研,一通操作下来,他们都以为他这是要在学术上深造的架势,结果最后毕业了竟然选择回临城当起了高中老师。
实在是大跌眼镜。
许凪远没见过简亓对谁有过好感,所以当简亓和他说自己谈恋爱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不信的,之后便是好奇,那人会长什么样。
现在见到面了,人确实是美的,只是未免太素了,少了些气质做点缀。
思来想去觉得总有些不对,脱口而出问道,“你这脱单了,小梧怎么办?”
简亓不喜,斜眼睨他,“关陈桑梧什么事?”
“好好好,不关不关。”
许凪远就是看这些年简亓一直单身,如今看他有了对象,提起旧人往事,时过境迁,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起来,“你说要是小梧当时没出国,你和她会不会就···?”
“别惹我骂你。”简亓鲜少愠怒,话不是说说而已。
许凪远收住了嘴,没再说什么扫兴话。
他也就一时感慨,当时大院里发小几个就小梧一个女孩子,从小就喜欢跟在简亓的屁股后面打转,大些了简亓不住大院里了,见不到面的那几年陈桑梧消停了些。
直到后面又考到了同一个高中,又死灰复燃了。
陈桑梧追求简亓的狂热,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也看不懂简亓到底她有没有意思,碍于陈家和顾家交好,简亓从未当着大家的面驳过小梧的面子,但也从没有接受过陈桑梧对他的好。
或许是被逼得太紧,有些烦了,直接跳了级。
小梧本来就比简亓小一岁,脾气是娇纵了些,事关高考,也不敢再去烦简亓了。
再后来,简亓考去了Z大,小梧也不知为何没有再嚷嚷着立志要考去省城和简亓读同一个大学,而是选择出国念书。
许凪远不是多管闲事的人,只是这些年自己当了老板,又是做荣记这样每天和无数人打交道的生意,看透了虚与委蛇。
人呢,也没前些年那么浪了,开始觉得有个门当户对又知根知底的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简亓一直单着,最开始他们就单纯觉得他那是洁身自好,可看到小梧一个人在英国这么多年,也从没见她接触过其他新的人,也是长情。
私下里难免自然地展开联想。
毕竟当年他们谁也不知道小梧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想出国了。
前段时间陈桑梧还找过他,问起了大家最近的现状,话里话外问的,其实还是尤其关注简亓现阶段的动向。
许凪远能怎么说,说简亓这位醉心教书现在已经打出招牌来的金牌教师,现在当然还是单身咯。
一个从小被捧为掌上明珠的女孩,因为赌气跑到国外念书,他是不理解的,可是听到小梧念念不忘这么多年,至此没有回响的时候,许凪远确实也是有点有意撮合的意思。
没想到等来的是,简亓和他说,自己谈恋爱了。
造化弄人啊,许老板长叹一声,不再自讨没趣,神叨叨地说缘分可遇不可求。
临走前又遇到了简亓这小女友回来,他当即绽开了个笑容,友好地打招呼自我介绍,“你好啊,我叫许凪远。”
女孩比方才从容,音色却比他想象里的绵软,极其有礼貌地微微鞠躬,不卑不亢地回握了他的手,“你好,我叫陶桃。”
许凪远心下了然,他大概知道简亓为什么喜欢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