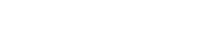【Papi】完
十二
“——死小鬼不信呐!!都说了绝对绝——对没在骗人好不好,真的超——火大啊当时,差点从窗户把她丢出去。”男人坐在贴墙靠门的一排金属长凳上,张牙舞爪连比划带嗷嗷,“怎么问都说不痛,稍一摸就像疼到死,张嘴闭嘴‘六眼就这啊’。现在回想起来都恨不得把死小鬼打飞……看着乖乖的小小一个,怎么气起人来这么要命呐!!你那边搞完了对吧?现在扔也没问题了对吧?扔坏了你会治的对吧?”
“再瞎嚷嚷就报给夜蛾了。”家人脱胶皮手套时瞥过去一眼,“不过教室楼层低,扔个几次又扔不死。要么你过两天再扔吧,扔完骨头又断了记得再抱过来。”
橡胶啪的一声响,被随手丢进垃圾箱。家人扭头下医嘱,“这三两天静养,能卧床卧床。卧不了床就尽量避免别被扔出窗。”刚说完又转向门边,“第一次出任务你没跟着?她没到能出单独外勤的时候吧。”
“没跟着早死了好不好。”男人背贴着墙滑了半寸像没骨头的猫,伸了伸胳膊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安排了两个一年生,这个,和杰养的小鬼头……那边聪明的很,一早自己藏好了就等我进去呢。但是这位了不起的小蠢蛋呢,脑子拎不清腿脚还成问题,没人帮着跑都没跑成。当时正好手机玩到快没电了就想着要么进去好了,谁知道呐,进帐一看完全超爆笑,小朋友正在咒灵打得火热欢天喜地玩抛接球呢——”
“你,是不是超喜欢被团成球到处扔呀?肋骨断四五根是不是很有趣呀?”路障一样直直伸着的腿只晃了晃光亮亮的鞋尖,示意话题所指。插完这句后,男人又仰着脖子“あぁあ”两声,有感而发,“我看是离嗝屁不远了……觉得有没有必要解剖?如果这个月要凑报告,到时候就给硝子尽可能把胳膊腿都捡回来。”
“还没放弃吓唬小孩呢是吧。那就能带尽量带,保持躯干完整就行,四肢意义不大。”家入站在窗边问,“晚上喝酒你一起吧,缺个人活跃气氛。我和七海说一声。”
“不要吧——,人家想补补觉诶——。”被无视拒绝的人左右活动抻了抻肩背脖子,站起身指了指,“那我把小家伙拎走了哦?”
家入点点头,只顾着摆弄手机。
你小声说谢谢家入小姐,家入小姐再见。
家入没抬头,只说好的不客气再见尽量少见吧。
被形容成玩抛接球也未免过于戏虐夸张。但比起被扭曲歪解的惨烈战况,两位高专教职工毫无人性的对话互动显然更为震撼。
被说成球的学生、被商量着扔出窗的小鬼、被规划好本月内遗体分配事宜的你,没昏迷没躺平意识清醒思维顺畅,甚至接受完反转术式救治耳聪目明身体倍棒——一直坐在旁边的简易床上,从始至终一清二楚超近距离听这俩人疯狂暴言的全程生放。
即便出发点大抵还是劝退,心灵所受的重创精神承担的激荡依然极真实。
是因为治疗结束时随口提了一嘴请家入帮忙看看手上的刺么?人家校医都证实了啊!轻微痛感来自划伤的小创口,但究竟那根小木刺是划了一下并没留在肉里,还是被捏着拔出来了,这谁也说不准啊。至于气到宣称学生是个球、威胁这就扔出去、顺便后事都一并安排好么?
想来有点委屈,胃痛都开始了。你把脸别去一边,躲开可能因姿势存在的直视目光,
“老师和家入小姐关系真亲密呢。”
话说完感觉不太对劲,又忙回头试图补充解释。
可对方闻言只垂了下视线,“あぁ、まぁあ。”两声,似乎并不想多说。
你便没有更多补充解释了。
十三
或许是因伤情位置的缘故,本次搬运与人为善采取了搂抱姿态,没一如既往扛行李般一把把你掀起来,用硬邦邦的大肩膀把人磕到吐。
但如此一来便会令人横生出些思春期的羞耻心。一时头向哪边扭都不对,眼睛看哪都成问题,两手两脚都颇感多余。
尤其在方才相当尴尬的半句对话后。
刚听完两人对自己的尸身处理决议——他们亲密到可以从产到销一条龙把你剖的明明白白。说不清的在意来的莫名其妙,忍不住把两眼都闭紧。
天气转热,温吞的风都带着暖意。室外光直直洒在眼皮上,视线里只剩橙红的光晕、起风时朦胧的树影,和沉默中冷不丁飘出来的轻轻一句,
“小东西,你再多受几次伤、多找几回死、多跑几次医务室,老师和‘家入小姐’的关系应该还会更‘亲密’哦?”
下意识便猛睁开眼,一时被夺目的光刺激到视野眩晕。用力眨巴缓了好一阵才重新看清,对方表情如常,眼罩下不知道视线落点在哪,但没低头。可能只是随口说的玩笑话,或许本人都没当回事。
他仰着脸歪着头嘟着嘴,唇峰亮盈盈的,像闲的无聊在吹什么小调。
幻听?一直在哼歌?刚刚那句是什么意思。
全身心戒备竖着耳朵,哼的旋律没你心跳声响。三四个气音还没合出旋律,只又听到对方突然提高音量,不知在和正撞见的谁打招呼,
“ハイハイィ、コンニチハっ。あっ、このコ?小家伙被咒灵当球踢着玩差点死掉了,老师正抱她去办退学呢。”
静默的走了一会,只这个挨千刀的时不时扑哧扑哧憋不住笑两声。
你把哭丧的脸捂起来,“请问您是以折磨欺负学生为乐么?”
“ヘェーーー、过分!”听声音,说话时正低头看你,“怎么可以这样恶意揣测老师嘛!!哪有在‘折磨欺负’你,明明才又刚帮某个小家伙把命捡回来吧?”
你说对不起谢谢您,风吹的树木裙摆都沙沙响。
他说道歉接受,虽然理解你听到“退学”两个字反应很大,但以后禁止像树袋熊宝宝似的抱着老师顺杆爬。
“不过呐,”男人掂着你晃了两晃。语气温和,尾音软软的。距离无限近,温温柔柔的两句,直往人骨头缝里钻,“就这么不想走?好好活着不好嘛?”
手心里扎扎的痒痒的痛痛的。你缩着脖子无处躲,只紧贴深色制服前襟把脸藏起来。
可能笑了一声也可能没有,隐约听见一句轻飘飘的“臭小鬼”。
“——死小鬼不信呐!!都说了绝对绝——对没在骗人好不好,真的超——火大啊当时,差点从窗户把她丢出去。”男人坐在贴墙靠门的一排金属长凳上,张牙舞爪连比划带嗷嗷,“怎么问都说不痛,稍一摸就像疼到死,张嘴闭嘴‘六眼就这啊’。现在回想起来都恨不得把死小鬼打飞……看着乖乖的小小一个,怎么气起人来这么要命呐!!你那边搞完了对吧?现在扔也没问题了对吧?扔坏了你会治的对吧?”
“再瞎嚷嚷就报给夜蛾了。”家人脱胶皮手套时瞥过去一眼,“不过教室楼层低,扔个几次又扔不死。要么你过两天再扔吧,扔完骨头又断了记得再抱过来。”
橡胶啪的一声响,被随手丢进垃圾箱。家人扭头下医嘱,“这三两天静养,能卧床卧床。卧不了床就尽量避免别被扔出窗。”刚说完又转向门边,“第一次出任务你没跟着?她没到能出单独外勤的时候吧。”
“没跟着早死了好不好。”男人背贴着墙滑了半寸像没骨头的猫,伸了伸胳膊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安排了两个一年生,这个,和杰养的小鬼头……那边聪明的很,一早自己藏好了就等我进去呢。但是这位了不起的小蠢蛋呢,脑子拎不清腿脚还成问题,没人帮着跑都没跑成。当时正好手机玩到快没电了就想着要么进去好了,谁知道呐,进帐一看完全超爆笑,小朋友正在咒灵打得火热欢天喜地玩抛接球呢——”
“你,是不是超喜欢被团成球到处扔呀?肋骨断四五根是不是很有趣呀?”路障一样直直伸着的腿只晃了晃光亮亮的鞋尖,示意话题所指。插完这句后,男人又仰着脖子“あぁあ”两声,有感而发,“我看是离嗝屁不远了……觉得有没有必要解剖?如果这个月要凑报告,到时候就给硝子尽可能把胳膊腿都捡回来。”
“还没放弃吓唬小孩呢是吧。那就能带尽量带,保持躯干完整就行,四肢意义不大。”家入站在窗边问,“晚上喝酒你一起吧,缺个人活跃气氛。我和七海说一声。”
“不要吧——,人家想补补觉诶——。”被无视拒绝的人左右活动抻了抻肩背脖子,站起身指了指,“那我把小家伙拎走了哦?”
家入点点头,只顾着摆弄手机。
你小声说谢谢家入小姐,家入小姐再见。
家入没抬头,只说好的不客气再见尽量少见吧。
被形容成玩抛接球也未免过于戏虐夸张。但比起被扭曲歪解的惨烈战况,两位高专教职工毫无人性的对话互动显然更为震撼。
被说成球的学生、被商量着扔出窗的小鬼、被规划好本月内遗体分配事宜的你,没昏迷没躺平意识清醒思维顺畅,甚至接受完反转术式救治耳聪目明身体倍棒——一直坐在旁边的简易床上,从始至终一清二楚超近距离听这俩人疯狂暴言的全程生放。
即便出发点大抵还是劝退,心灵所受的重创精神承担的激荡依然极真实。
是因为治疗结束时随口提了一嘴请家入帮忙看看手上的刺么?人家校医都证实了啊!轻微痛感来自划伤的小创口,但究竟那根小木刺是划了一下并没留在肉里,还是被捏着拔出来了,这谁也说不准啊。至于气到宣称学生是个球、威胁这就扔出去、顺便后事都一并安排好么?
想来有点委屈,胃痛都开始了。你把脸别去一边,躲开可能因姿势存在的直视目光,
“老师和家入小姐关系真亲密呢。”
话说完感觉不太对劲,又忙回头试图补充解释。
可对方闻言只垂了下视线,“あぁ、まぁあ。”两声,似乎并不想多说。
你便没有更多补充解释了。
十三
或许是因伤情位置的缘故,本次搬运与人为善采取了搂抱姿态,没一如既往扛行李般一把把你掀起来,用硬邦邦的大肩膀把人磕到吐。
但如此一来便会令人横生出些思春期的羞耻心。一时头向哪边扭都不对,眼睛看哪都成问题,两手两脚都颇感多余。
尤其在方才相当尴尬的半句对话后。
刚听完两人对自己的尸身处理决议——他们亲密到可以从产到销一条龙把你剖的明明白白。说不清的在意来的莫名其妙,忍不住把两眼都闭紧。
天气转热,温吞的风都带着暖意。室外光直直洒在眼皮上,视线里只剩橙红的光晕、起风时朦胧的树影,和沉默中冷不丁飘出来的轻轻一句,
“小东西,你再多受几次伤、多找几回死、多跑几次医务室,老师和‘家入小姐’的关系应该还会更‘亲密’哦?”
下意识便猛睁开眼,一时被夺目的光刺激到视野眩晕。用力眨巴缓了好一阵才重新看清,对方表情如常,眼罩下不知道视线落点在哪,但没低头。可能只是随口说的玩笑话,或许本人都没当回事。
他仰着脸歪着头嘟着嘴,唇峰亮盈盈的,像闲的无聊在吹什么小调。
幻听?一直在哼歌?刚刚那句是什么意思。
全身心戒备竖着耳朵,哼的旋律没你心跳声响。三四个气音还没合出旋律,只又听到对方突然提高音量,不知在和正撞见的谁打招呼,
“ハイハイィ、コンニチハっ。あっ、このコ?小家伙被咒灵当球踢着玩差点死掉了,老师正抱她去办退学呢。”
静默的走了一会,只这个挨千刀的时不时扑哧扑哧憋不住笑两声。
你把哭丧的脸捂起来,“请问您是以折磨欺负学生为乐么?”
“ヘェーーー、过分!”听声音,说话时正低头看你,“怎么可以这样恶意揣测老师嘛!!哪有在‘折磨欺负’你,明明才又刚帮某个小家伙把命捡回来吧?”
你说对不起谢谢您,风吹的树木裙摆都沙沙响。
他说道歉接受,虽然理解你听到“退学”两个字反应很大,但以后禁止像树袋熊宝宝似的抱着老师顺杆爬。
“不过呐,”男人掂着你晃了两晃。语气温和,尾音软软的。距离无限近,温温柔柔的两句,直往人骨头缝里钻,“就这么不想走?好好活着不好嘛?”
手心里扎扎的痒痒的痛痛的。你缩着脖子无处躲,只紧贴深色制服前襟把脸藏起来。
可能笑了一声也可能没有,隐约听见一句轻飘飘的“臭小鬼”。